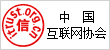作者简介: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著有《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等。由于历史的错位,一个科学家,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为国家利益驱使,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弃学从政,官至一品。但最后留在历史上的,竟是一纸辛酸。 谈到现代中国的科学家,大概要数地质学界诸位最令人刮目相看。从丁文江到翁文灏、李四光,不仅专业上响当当,而且个个行政能力极强,都是治国平天下之才。尤其是翁文灏,官至“宰相”一级,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仕途的极致。 翁文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向对做官兴味索然,偏偏仕途对他敞开了大道。1932年春天,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翁文濒自然乐于前往。没想到他与蒋大概是前世有缘,这么多前去布道的“帝王师”中间,蒋对翁文灏竟然情有独钟。蒋喜用浙江人,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又算得上蒋的宁波小同乡。他忠厚诚笃,又颇具才干,是蒋最欣赏的那种德才兼备之人。于是,蒋当下就邀翁文灏留下,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举,再三推辞而不得,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翁文灏则挂一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发表他为教育部长。翁文灏又藉口“丁忧”,为继母守孝而坚辞不就。 不过,翁文灏的挂牌南京,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南京政府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携手合作的开端。与翁文灏同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挂牌的,还有胡适之、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在上一面,蒋介石也知道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搞专家治国了;而在下一面呢,本来向南京争人权,要法治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开始认同政府的合法性了。 翁文灏尽管挂的是头牌,但在这一大帮知识名流中,翁文灏的庙堂意识恐怕是最淡的。他不是缺乏行政的能力,只是少了一点做官的兴趣。翁文灏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土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翁文灏有自己的专业关怀,而这样的关怀同样具有救国救民的功能,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命运真是不可违拗,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翁文灏的整个人生。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介石得报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还派来医生,接来家属,将这个体重仅九十磅的垂危病人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如果说庐山讲学,翁文灏对蒋介石的“不耻下问”有“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武康脱险之后,无疑又加了一层“救命之恩”了。以翁文灏之忠厚,不可能知恩不报。当第二年蒋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无法再推托了,于是正式入京,与蒋廷黼等人一起,从此弃学从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虽然是迫不得已,但起初也未尝不雄心勃勃。在《独立评论》时期,翁文灏就自信将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熟悉二十年代《努力周报》的人们都知道,翁文灏的政治观显然是二十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鼓吹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疑。翁文灏是否受丁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确都有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翁文灏以如此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起步政坛,既有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满足感,同时也不乏科学家的自信。传统的“好人政治”到了现代,虽然内中的灵魂未变(仍然以“好人”为核心),但“好人”的内涵毕竟有所演变。“好人”不仅要有儒家式的道德修养,而且也要具备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管理能力。而后者,正是丁文江、翁文灏他们这些科技专家所赖以自豪的。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了。 那么,好人当政的结果又是如何?蒋介石主政的整个三、四十年代,至少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1935年的“人才内阁”和1948年的“行宪内阁”。每当濒临危机时,蒋介石总是选择翁文灏这样的公认的才俊组阁,以期挽狂澜于未倒。在这两次实验中,翁文灏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1935年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十三年以后又进一步由他出面组阁,连司徒雷登也为此欢欣鼓舞,以为将开出“行宪”后的“新气象”。可惜的是,翁内阁仅仅存在了六个月零二天就呜乎哀哉。从表面来看,翁文灏是被那个自以为是的王云五所误(这个商务老总以为推广金元券就像推广他的四角号码词典一样简单),实际上,国民党腐败到那个份上,即使市制改革成功,也最终难免一败。政治体制不变革,纵然有一打翁文灏这样的好人当官,又何尝能补大局于万一? 翁文灏的悲剧几乎是宿命的。“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他,仅仅凭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无法扭转一个专制体制必然厄运的。这样一个体制,总是扼杀具有宏大眼光和变革意识的真正的政治家,只会将本来更适于坐在处长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错置于部长甚至更负责的高位。在这种体制中,阴差阳错的翁文灏与其说是幸运儿,倒毋宁说是牺牲品,一个为腐败体制陪葬的牺牲品。 尽管翁文灏是不懂政治又误入仕途的一介书生,但他毕竟是一个“极明察”之人。到1948年底,当他看清了这个政权的症结所在,便决意与跟随多年的“恩主”分手。在蒋介石的另一宠臣陈布雷服药自杀,为蒋殉葬的时候,翁文灏却不顾蒋的再三挽留,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翁文灏与陈布雷在经历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差不多是同龄之人,且都是蒋所信任的宁波人,两人皆书生本色,都是一再推辞而不得,捱到1934年,才前后到蒋的身边就职。同样的士报知遇之恩,同样的士为知己者而死,同样的到1948年底看清大势,顿悟人生。相比之下,陈布雷的传统文人气太重,竟然弃世而去,临死前的遗言中还对蒋战战兢兢、忠诚不贰。而翁文灏,毕竟在欧洲接受了四年西洋的教育,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虽然身上还残留着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习性,但整个人格较之陈布雷已经独立了许多。同为救国心切,陈布雷无法将国家与蒋氏王朝区别开来,翁文灏却能在最后一刻发现两者之间的疏离,并决然弃蒋而去,投入和平的阵营。在纠正错误这一点上,翁文灏倒表现出了科学家的潇洒本色。 1950年初,翁文灏在英国拜访李约瑟爵士,目睹昔日老友著作等身,学业鼎盛,不由得触景生情,黯然伤神。一个科学家,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为国家利益驱使,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弃学从政,官至一品。但最后留在历史上的,竟是一纸辛酸。如此结局,又如何不让人悲哀! 在现代中国,像翁文灏这样既有传统功名(早年曾经中取秀才),又有洋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是少而又少的。半中半西,本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时代印记,翁文灏的所有悲剧似乎都可以在他的知识背景中找到某种解释。如果有幸遇上一个太平盛世,一个开明体制,也许还不至于牺牲得如此廉价。然而,种种错位,种种短拙,竟然巧合在一起!翁文灏,究意是你负时代呢,还是时代负你? (责任编辑:PAUL ZENG) |






 为侨海网专有标识。侨海网权属世界华人杂志社、洛杉矶国际时事通讯社、侨海网有限公司。
为侨海网专有标识。侨海网权属世界华人杂志社、洛杉矶国际时事通讯社、侨海网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