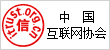|
一,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绿色”反思 在改革前的中国,尽管宣传上作为“资本主义罪恶”时常提到西方的环境污染,但从未承认中国自己有什么环境问题。相反,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都把“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当成理想美景。中国的环境生态保护运动是改革时期在西方“绿色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80年代翻译的《增长的极限》、对《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介绍都起了至关重要的“绿色启蒙”作用,今天国际上比较熟悉的中国两种绿色声音:实际从事环保维权的环保NGO组织,和并不怎么参与维权、却喜欢在国际上发言的“新左派”朋友都深受这种影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环保思潮在基本价值观上是普世性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需要环保,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在问题意识上却是高度“西方化”的(即认为中国环境问题的发生机制和当代西方相同,甚至就是一种“西方祸害”的东渐)。相对而言,环保NGO的诉求更突出前者,而“新左派”的环保观更突出后者。这就造成一种现象:西方绿色思潮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特征:从反思工业化、反思资本主义到反思“西方文明”、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一些绿色思潮的宣传者却有“喜欢西方的反思,却不喜欢反思自己”的特点。不少人认为,环境破坏只是西方带来的问题、“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现代性”(尤其是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新左派”朋友更喜欢这三个说法。但我认为西方人这样讲是一种反思精神,我们也跟着讲,就没有反思精神了。我是很赞成环保的,但我历来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思想要自立”,在中国讲绿色思潮是要有自己的针对性的。 现代环境保护运动起源于西方,但环境破坏是个人类的问题,不能说是起源于哪里,人的欲望与环境制约有矛盾,“竭泽而渔”与“细水长流”两种态度也都源远流长,很难说某个文明持一种态度另一个文明则只有另一种态度。历史上很多非西方地区都出现过因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灾难,乃至导致一些文明的消亡。有人说中国有天人合一学说,可以保护环境。其实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是一种以“宇宙等级秩序”来证明人间等级秩序(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理论,它与环境保护本不相干。如今人们把环保意识附会于它,倒也不无可取,因为作为符号的语言能指在历史中增添新的所指,所谓古为今用,作为宣传手段也是有用的。 问题在于环境保护决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认识问题。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所谓“重视环境”只能流于空谈。由于经济学上所谓外部性,人人明知重要而又人人破坏之的事例不胜枚举。筒子楼里公共水房往往污秽不堪,就是一个例子。我国古代虽不像一些古文明那样环境破坏到了文明消亡的地步,但环境问题确实也不小。远的不说,明代的《徐霞客游记》中在江西、浙江、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一路,都记载了严重的环境破坏,造纸业污染河流、烧石灰污染空气毁灭风景、乱砍滥伐使“山皆童然无木”,生活垃圾使永州、柳州等地的许多名胜堙为“污浊”的“溷围”。还有学者认为历史上黄河水患最严重时期就是因为从游牧变成过度农耕的缘故。如果说那时没有出现尾气、酸雨和核污染,那只是因为古人还不懂得相关工业技术,而不是因为他们懂得“天人合一”。 很多人认为改革时期“单纯追求GDP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当然有这个因素。不过改革前中国经济混乱时,环境生态问题也并不轻。大跃进不仅造成大饥荒,也造成空前的生态灾难,“大炼钢铁”毁灭了森林,三门峡工程把水利弄成“水害”。只是那时严重的问题是饥饿,环境问题没人讲。实际上那时这个问题就很大。例如那时我国农业尽管化肥农药没有今天用的那么多,但那时的化肥农药品种对生态的破坏比今天的品种可要严重得多。改革前我国不少地方大量使用廉价的氨水(我至今难忘那呛人欲晕的刺鼻氨气和水田施过氨水后田螺蚯蚓都死光、连田埂的草都熏枯的情景)做当家化肥,一些地方还使用有毒的石灰氮。那时用量最大的农药还是西方早就禁用了的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的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以及剧毒、高残留有机磷(一六零五、一零五九、三九一一等)、汞制剂(赛利撒、西力生)等。这些东西对生态的危害要比现在的品种大多了。我在农村时亲眼看到当时对六六六的滥用:不但用于田间,还被当地人用于熏杀马蜂(马蜂蛹和幼虫是当地美味)、用于毒鱼以取食。可悲的是农民并非不知这样取食有害,只是饥不择食啊。那时提倡的“五小工业”更是效益小污染大的典型。 而改革前的文革时代恰恰是“政治挂帅”,不要说GDP,当时几乎所有经济数据都是“机密”,提都不能提,邓小平抓生产,就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属于反动的“修正主义”。那时考核官员更不是考核他治下的经济增长,而是考核他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作为。总之,那时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与其说是因为“追求经济增长”不如说是因为“追求巩固权力”而造成的。 不只中国,其实德国也有类似现象,我们知道当年的“社会主义”东德生态环境要比“资本主义”西德差得多,也比统一后更差。如今绿党在前东德地区支持率比前西德地区小得多,我猜原因可能是经历过东德生活的人对“反思资本主义”的绿色思潮不那么感兴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改革时代我国的“政治挂帅”变成了“经济挂帅”,1990年代后更走向“GDP挂帅”,由此我们陷入了今天的环境危机。于是人们呼吁改变追求目标,另换考核方式,升官不靠GDP,而要考核环境,有人还设计出“绿色GDP”之类新型考核指标。可是如果以前的“政治挂帅”同样造成环境破坏,今天从“经济挂帅”改成别的什么挂帅,哪怕就是“环保挂帅”就可以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追求”什么、“考核”什么不能说不重要,但追求与考核的主语--谁有权“追求”,谁来“考核”,可能更为重要。一个权不受制、责不可问的体制无论名义上“追求”什么,都可能与民众的期待距离甚大,甚至南辕北辙。中国现在一方面也提可持续增长,建设生态文明等,一方面环境却不断恶化,就是这个道理。 二,“绿色公共干预”还是“绿色市场交易”:矛盾与互补 这就涉及到了绿色思想的另一个层面即制度层面。如前所述,我认为环保不仅是个认识问题,更是个制度安排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似乎也是西方绿党的认识。我理解德国绿党主张的“四大支柱”-- 生态智慧、基层民主、非暴力、社会正义,和2001年“全球绿党宪章”提出的“六大原则”,即上述四项加上“可持续发展”和“尊重多样性”,其实都体现了许多制度创新思想。当然,这方面的争论也不少。正如过去“资本主义的西德”与“社会主义的东德”都出现过环境问题一样,今天解决环境问题也有许多思路,不过在我看来基本还是两种:一是通过“公共利益干预”去限制、乃至禁止污染,二是通过“个别利益诱导”去换取减污,乃至弃污。前者寄希望于国家以及公民社会(环保NGO等)对排污主体(个人或企业法人)唯利是图行为的制约,可以视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设想,按我的理解,欧洲的绿党比较接近这种主张。后者以如今风行的“碳交易”(又名“排污权交易”)为代表,希望靠市场机制而不是靠强行管制,使排污主体能够为牟利而自愿减少或放弃排污,可以视为一种“生态资本主义”主张。 我知道在西方两者有很大的争论。排污权交易设想一直被西方左派强烈批评为邪恶的“空气私有化”,而靠国家管制控制污染又被右派看成是可怕的“大政府幽灵”。但是我觉得,正如现代经济往往是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某种结合一样,在环境治理方面市场机制和公权力管制何以就不能并行?实际上,管制限污和交易减排都有成功的例子但也各有局限性,至少在中国,我不认为两者是完全排斥的。 但是在中国,正如我常常担心既没有市场自由(由于政府权力太大)、也没有福利国家(由于政府责任太小)一样,环境方面我同样担心“碳交易”成为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而“碳管制”又成为政府滥用权力的说辞。大家知道我对中国改革的基本主张是“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在环境问题上我同样认为限权与问责两者都是走向“中国式绿色”的道路。与西方人争论“政府,还是市场?”不同,中国的“政府”与“市场”与西方都不一样。正如两德并存时期布莱希特讽刺说:在东德“如果人民不喜欢政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散人民,另外选举一个人民”。类似地,西方自由市场曾被批评为“赢家通吃”,但中国的“市场”主要弊病却是“权家通赢”,所以在中国,争论“政府还是市场”之前先要解决“政府”本身的改革和“市场”本身的公平问题。 而据我所知,绿党与左派一样对“排污权交易”并不欣赏,但在“公共利益干预”方面,绿党不同于强调民主国家作用的传统西方左派之处,在于她更强调以NGO方式行动的“公民社会”来干预,这就是作为绿党思想四大支柱之一的“参与式民主”的主要内容。但是众所周知,在今天的中国,NGO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如果说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这里的“政府干预”与“公共利益干预”不是一回事(最明显的证据是:德国历史上甚至连马克思这样激进的自由市场批判家也不主张当时那种非民主的国家干预和国家管制,相反,他明显地认为魁奈、亚当斯密这样的自由市场论者还比柯尔贝、李斯特这样的国家干预论者进步),那么NGO式的公民社会干预在中国就更是任重而道远。绿党“参与式民主”本意是有了宪政民主国家还不够,还要让自由公民通过NGO之类的形式直接参与治理,可是在中国,可能您不了解的是“参与式民主”的说法很盛,“宪政民主”却是不能说的,NGO更被压得似有似无,最近连“公民社会”都成了敏感词!那么这种条件下的“参与式民主”是什么?就是在严防宪政民主、打压公民社会的同时让臣民有所“献言献策”,以供主上参考取舍。这难道是绿党所提倡的参与式民主吗?环境问题可以在这样的体制下解决吗? 不过,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与一般的国家治理还是很不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环境和污染都是无国界的。如果说西方如今的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虽有弊病毕竟还一直有效,结合两者的“社会市场经济”更是成绩卓著,那么在环境治理方面,无论“管制限污”还是“交易减排”都会碰到全球治理机制欠缺的困难。这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以“碳交易”为内容的京都议定书的长期拒绝。其实我们知道,与欧洲的福利国家相比,美国在西方是更强调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根据地,以“碳交易”而非“碳管制”为内容的京都议定书应该说更多地体现美国人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左派舆论对这个被斥为“空气私有化”的议定书批评很厉害)。但是尽管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一些州“碳交易市场”起了一定作用,在真正关键的全球碳交易问题上美国却不合作。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机制,能像民主治理机制在一个国家内那样维护交易规则,打击欺行霸市。国际上没有这种约束,美国就是要“免费排污”,不肯为排污权付费,哪怕这个排污权交易符合他的价值观,但抽象的价值观在具体的利益面前往往苍白无力,尤其在行为不受制约时更是如此。 而国际社会之所以推出京都议定书式的交易减排,也并非“新自由主义”有多大影响,而是由于“碳管制”对治理机制的要求比“碳交易”更高,犹如“全球福利制度”比“全球市场”更难以实现一样。连碳交易有人想不接受就可以不接受,要搞碳管制岂不更困难? 所以我认为,在现有的民族国家内民主治理体制下,国界内的环境问题无论是“管制限污”还是“交易减排”都是有作用的,两者还可以结合起来增强环境治理效果。但是对于全球环境问题而言,两者都遇到了缺乏全球治理机制的障碍,而由于西方本来就是多元民主的,两者各自的“无效”似乎就成为对方批评的理由。但我认为,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如何建立全球治理机制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挑战(不仅仅是环境挑战),这方面我对欧洲寄以希望,因为欧盟虽然不是全球治理机制,但毕竟是有史以来相对而言最成功的跨国家治理机制,对于欧洲范围内的环境治理也能发挥作用。尽管它在最近的“欧债危机”中经受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考验,但我希望她成功,并且以跨国治理实践为未来可能的全球治理提供经验。 而未来全球治理意味着“全球化的民主”,它的必要条件(尽管可能不是充分条件)应该是参与治理的各个国家首先具备国内的民主,就像欧盟只能是民主国家联合体一样。因此在中国,我认为绿色思想首先应该是民主思想,而且参与式民主也只有在宪政民主基础上才有意义。没有国内的民主治理机制,无论“管制限污”还是“交易减排”首先在国内就会遇到障碍,更不用说没有中国这个大国的民主化就更谈不上全球治理的民主机制了。 三,民主与社会正义遭遇“纯经济全球化” 对于欧债危机,去年我写过一篇论文叫《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大意是: 西方发生债务爆炸,传统的“左右之争”或“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之争”就涉及了危机责任问题。一派说危机的原因在于太自由放任,尤其是金融自由太多;另一派说原因在于高福利太过分,造成开支失控。然而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 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都各有利弊,但仅就债务而言,理论上无论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还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都可以在财政均衡条件下运作,至少不至于无限远离均衡、导致债务爆炸。但是,民主制下有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即左派、右派要得势,都得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对左、右的主张都只喜欢一半,所以左派上台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上台减税容易,减福利难;这就导致宪政制度的基本目的即我以前称之的“天平效应”受到破坏。如此往复循环,债务窟窿就难免越来越大,终于导致窟窿塌陷的大祸。 换言之,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指出左右派的主张各有什么毛病,但有毛病和不能继续运转是两回事,现在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搞到难乎为继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哪一种主张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两种主张在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的情况下都“只能实行一半”的结果。而“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机。 这次德国的大选又一次证明了我的看法。如所周知,本次大选基民盟获得大胜,社民党得票也有增加。但绿党和自民党都吃了亏。为什么?因为绿党要求增税,自民党要求减福利,德国人民都不喜欢。而基民盟要求减税(至少反对增税)但却回避减福利,社民党要维护福利但却回避增税,两者都得到大量的支持。可问题是,只增福利不增税,或者只减税不减福利,那赤字和欠债不就越来越多了吗?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德国会变成今天的希腊! 但是民主制度如果一直就这样搞,它还能走到今天?民主国家过去的辉煌成就又怎么能取得呢?我曾指出:在没有今天那种全球化局面以前,一国经济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是玩不了几天的,而民众不是圣贤,但也不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傻瓜,他们感到出了问题就会改变。事实上,民主国家历史上民众接受增税与接受减福利的例子都很多。甚至在波兰等东欧国家,恰恰是民主化使得民众愿意减福利的。那么为什么那些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众现在变得如此“执迷不悟”?与1990年的波兰人相比,当然是因为当时波兰人用有限的减福利换得了他们过去没有的自由民主,而今天的老牌民主国家却没什么可换,那么与这些国家的过去相比呢? 我的回答是:其实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与“全欧化”)、但宪政民主治理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因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 比如我们也有左派和右派,可是我们的“左右互动”却跟你们相反:皇上最喜欢增税,同时却讨厌民众向他问福利之责。所以我想,如果你们的绿党和自民党能够放弃民主而拥护专制(恕我冒昧地作这种令人不快的假设),那么你们的“增税”和“减福利”主张在我们这里都会受到重用!“左派”帮他增税,“右派”帮他减福利,难怪我们会有个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府。现在有些人在议论中国“政府债务危机”的可能。我说你们这是操西方人的心,在中国如果出现政府债务危机,那可能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大进步了!大家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老百姓大量饿死、而政府却自豪地宣布“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奇观吗?假如皇上能够随意横征暴敛,同时老百姓又不能向他追索福利,甚至饿死了都不能抱怨,他怎么还会欠债?恐怕他担心的是钱多得不知怎么花了吧?这时如果有人要借,那不是求之不得吗? 这样两种相反的国家(当然,由于都有“左”也有“右”,人们有时没觉得相反)共同玩“经济全球化”游戏,结果可想而知:左右都要讨好民众的国家向左右都要讨好“皇上”(专制者)透支,前者掩盖了窟窿,后者避免了“过剩”,前者得到高消费,后者得到高增长。表面上是各得其所,但两种体制的弊病(相反的弊病)却日益发展。后者的社会不公、官民矛盾、腐败蔓延,包括牺牲环境等积弊无法纠正,出现“越维越不稳”的困境。而前者有这种透支机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希腊“入欧”后钻“货币全欧化,财政国家化”的空子透支欧洲,美国在全球化中利用美元透支国际市场,尤其是透支中国这样的“低人权国家”,都是这样发生的。 对于欧债危机我曾指出:今天欧洲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选择,如果不强化欧洲的政治一体化(首先是财政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就保不住。而近期的欧洲选举表明,“逆水”中的欧洲“进”则举步维艰,“退”则后果严重。这一次的左右轮替,其实仅就“左”“右”本身的理念而言意义并不大,欧洲民主制度下左右轮替的“政治钟摆”已经不知多少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谁战胜谁”。但这是正常状态下“天平效应”的摆动(即财政相对平衡前提下“高税收高福利”与“低税收低福利”的轮回),还是“反向尺蠖效应”下旧弊的积累(左派能增福利难增税,右派难减福利易减税,导致财政越来越失衡)才是问题的关键。 而对于全球化就更是如此。绿党一直强调社会正义,我在中国也从1990年代就以“公正至上”的主张闻名,但是我想您也同意,这些年西方与中国的社会不平等都在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政治体制和人权标准的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 理论上,一体化经济中资本与商品的梯度流动(资本流向不发达地区,生产出廉价商品流向发达地区)应该有益无害。但是在体制不同、而人的流动性比资本与商品流动性小得多的情况下,这种流动会带来国别差距缩小而一国内差距扩大的结果。我们知道,发达民主国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但在经济总量、而且在经济平等方面进步巨大。劳资生活差异和贫富差距在缩小,基尼系数、主要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在降低。对于这些成就,有人强调民众运动、工农组织、民主压力和再分配的效果,而另一些人则强调自由经济中要素稀缺格局发生变化的效果,即市场经济的要素契约中总是稀缺要素持有者占据谈判优势,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稀缺,劳动相对过剩,因此资本的谈判实力远超劳动,导致两者差异巨大。后来资本积累到越来越过剩,劳动变得相对稀缺了,劳动的谈判实力就上升,两者的谈判地位就趋于相当了。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斥的。一百多年来发达民主国家社会平等尤其是劳资关系的进步,其实是民众、劳工维权运动压力和资本积累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的综合结果。 但是单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和民主国家再分配的压力,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廉价商品输入又替代了本国的产业,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很反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实际上,资本流出后在“低人权国家”搞血汗工厂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国劳工就业机会损失却降低了收入,这就导致即便全球化也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趋势却明显逆转。发达国家的劳工发现他们如果不向“低人权国家”的血汗劳工看齐,就“丧失了竞争力”。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权国家的强势者却通过这种全球化中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其收入也向发达国家的富人看齐(甚至由于权钱结合更方便可以比西方富人还富)。这种“中国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的趋势在两边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初始分配差异的扩大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中的资本外流又导致税基萎缩,国家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降低。尤其是在“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下,资本流出后就不再对本国福利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福利需求和福利提供能力的反差越来越大,而这个反差也只能靠全球化中的透支功能来弥补。发达国家的透支越来越厉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四,“反全球化”不可取,应该在社会正义基础上深化全球化 “中国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自然在中国也引起了严重的不满。于是“反全球化”思潮也传入了我国,尤其是力主反全球化的西方左派在我们这里的一些“左派”朋友那里很容易找到知音。 但这当然是大错特错。前面说过西方的左派“反全球化”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确实是降低了他们劳工的谈判地位。但是,对于资本流入、商品流出的中国来说,其逻辑导向本来应该完全相反:如果纯就经济因果而言,这样的流动应该在中国导致资本趋于相对过剩,劳动趋于相对稀缺,这本来应该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全球化本来应该造成一个“中国劳工趋同西方劳工”的走向,而不是仅仅有“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应该说这一走向也不是完全不存在。这些年来我国劳工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都有不少进步。这种变化与上面讲的全球化中“要素稀缺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与西方是反向的)倒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问题在于这一走向还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中国富豪攀比西方富豪”的走向却比逻辑上应有的更加凸显(主要指有权力靠山的富豪)。这就要归因于政治体制了。这种体制人为压制了劳工和其他弱势者的市场谈判权利。关键的问题在于: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社会主义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是不合逻辑的。在劳工权利与现代工会运动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派拒斥“纯经济全球化”以维护本国劳工的谈判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劳工尚无结社自由、而全球化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却有利于劳工的中国,如果也有真正的左派,他们应该做的是当然不是拒斥全球化,而是努力把全球化从纯经济层面推向全方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为劳工争取政治权利,使全球化提高中国劳工谈判地位的效果能够充分体现,防止这种效果被“专政”所人为压制。 而就西方而言出路何在呢?这是我应该请教您的问题。不过我可以讲几点看法供您批评,可能很可笑,但对朋友无所谓吧。 首先由于我刚才讲的原因,社会正义在中国无法回避民主化,而中国的民主化现在对于西方已经不是价值观上同情的问题,尤其对于西方的左派和劳工而言,在如今这种全球化之下由于刚才提到的机制,如果中国的劳工不能像你们的劳工那样维护权利,有一天你们的劳工就会像中国劳工那样失去权利。在目前的全球化下“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不是不可能的!靠贸易保护主义切断经济全球化不是办法,进一步透支维持高福利也不是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出路只能是用人权的全球化充实如今的经济全球化。 这当然不是很快能实现的。而在此之前,还有两个治标不治本的主张: 第一是“遭遇全球化”的民主体制恐怕得调整游戏规则。也许不必去反对福利国家,但需要适当限制议会权力,即立法禁止议会通过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超标”(例如可以参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欧洲标准”: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的不合理预算。换言之,想要高福利就必须接受高税收,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适当限制议会权力本是民主制度的通例,例如很多民主国家都以宪法规定议会不得取消言论自由。而上述限制本来也是符合常识的,否则也不会列入《马约》。以往在没有全球化的时代,由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根本玩不久,基于常识议会一般也不会这么不负责任。但全球化时代就不同了,《马约》之所以设立上述门槛就是看到“全欧化”带来一国议会不负责任的风险,但是事实证明在欧洲一体化没有包括主权层面、《马约》也没有变成“欧洲合众国宪法”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在形成“超国家民主”之前那些高度参与全球化游戏的民主国家有必要把它列入宪法来约束自己。 第二就是废除“防止双重征税”的规定,使“双重征税”合法化。以此适度约束资本流动,要比搞贸易保护、通过传统的关税壁垒限制商品流通更为合理。在人力不能跨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国国民努力形成的资本转移到别的国家,尤其是转移到成本畸低的“低人权国家”,会使本国损失就业机会、增加福利需求。但是“防止双重征税”又会导致税基流失。两相夹击,是使发达民主国家走向无限制透支道路的一大因素。不应该行政限制资本流动(对于资本流入国的劳动者尤其如此,理由如上所述),但是资本追逐低成本所产生的额外收益应该对母国的社会公益有所补偿。当然它也应该对流入国尽公共义务。如果它希望既追逐低成本又不愿增加税赋,当然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整个公司作为法人、甚至所有者作为自然人都迁入流入国,完全成为流入国的公司(因而也就没有了双重征税的问题),从而承担“低人权国家”的产权风险。不能既在民主法治国家注册享受其产权保护同时却无需纳税,又享受“低人权国家”的畸低成本带来的额外收益。 总之,如今深度与广度都大为发展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与全欧化)确实给一国主权下的宪政民主机制出了难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宪政民主机制的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与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政治一体化(欧盟就体现着这一方向,但现在她面临着危机“倒逼”的压力)。但是在这个根本问题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改进制度设计,降低如今这种纯经济向度的全球化带来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五,民主仍然是世界潮流,但民主也必须与时俱进 这个世界上历来有很多人为专制唱赞歌,要驳斥这些东西并不困难。但真要有效地推进宪政民主,也不能把宪政民主浪漫化。这种机制并不完美,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还会不断碰到新问题、新挑战。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文明一定战胜野蛮,历史上民主制度的衰败(不含那些民主诽谤者渲染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失败)不止一次,古代在希腊、近代在欧洲也多次有过专政战胜民主的教训,没有理由认为今后就不再可能出现类似悲剧。民主国家必须好自为之。 同时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要看清一点:欧洲国家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中的民主制”逻辑上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民族国家”(例如欧洲如果能真正走向政治一体化,能够避免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国家化的冲突),或者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二者只要缺一,都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样的事态恰恰表明,欧洲的民主绝不是什么虚伪的民主。如果只是在“民主”的外衣下搞独裁制或寡头制,不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大多数”,而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皇上,或者讨好一小撮为富不仁者,那即便在民族国家条件下欧洲也不会有现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有近代以来民主国家的辉煌。而那些左右派都无需讨好老百姓、只需看皇上或寡头们脸色的国家,是不会出现如此“奢侈”的问题的——犹如饥民不会患上肥胖病。但是这些国家有其更为深刻的大弊。而在解决这些大弊方面,我们是可以互相启迪的。 (责任编辑:PAUL ZENG) |






 为侨海网专有标识。侨海网权属世界华人杂志社、洛杉矶国际时事通讯社、侨海网有限公司。
为侨海网专有标识。侨海网权属世界华人杂志社、洛杉矶国际时事通讯社、侨海网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