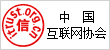|
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这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要思考的问题。有学者对南北战争的研究表明,美国建国的政治基础不是签订社会契约,而是牺牲,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政治神学。因此,美国建国的政治事件不是费城会议,而是独立战争,不是1789年合众国宪法,而是1776年独立宣言。如果用施密特的话来说,1789年制定的不过是宪法律,而1776年奠定的则是绝对宪法。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建国的首要问题乃是分清敌我关系,即究竟谁才能够作为“我们人民”的一部分参与到建国中,而恰恰是由于敌人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变成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具体来说,恰恰是由于英国人的存在使得美国13个州认识到自己作为“我们人民”的政治意义。所以美国宪法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人民”。这是在政治上的敌我划分清晰之后才能够出现的概念,也是在绝对宪法已经完成之后才能够出现的概念。而无论是牺牲、无论是绝对宪法、无论是敌我概念,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神学的意义上才能理解。 9·11之后,重提政治神学、重提施密特的敌我概念已成为美国政治哲学和宪法学中的显学。早在9·11之前,也就是科索沃事件之后,美国和欧盟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即究竟采取社会契约思路的欧盟模式,还是采取敌我划分的美国模式。哈贝马斯等人认为通过协商对话或社会契约可以重建全球秩序,欧盟的形成就是一个例证。可是,这种社会契约论的模式遭到了美国的嘲讽。美国人认为,如果不是美国人在敌我概念的基础上把当年的苏联人和今天的伊斯兰人挡在了外面,欧洲怎么可以享受如此悠闲的后现代生活?这就是卡根所说的“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水星”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欧洲的阿拉伯移民问题以及今天的利比亚战争问题,都说明社会契约存在着自己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条件,那么社会契约建立的无疑是全球政府,而不是国家。而美国人在9·11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行动,恰恰来自对牺牲概念的理解,即必须用牺牲来捍卫美国宪法,这既是当年林肯在南北战争中所做的,也是今天在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所做的。 但问题在于这种美国例外主义政治神学在美国一直受到自由主义的挑战,受到文化左派的挑战。在文化左派看来,美国例外主义乃是蒙昧主义的产物,是一套意识形态宣传。恰恰是依赖这一套形态宣传,使得美国卷入到形形色色的对外战争中,从越战一直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由此,正如Paul Kuhn所言,美国今天面临的挑战类似当年基督教面对新教改革的挑战,因此他认为政治神学今天面临着全球新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挑战。 (责任编辑:PAUL ZENG) |






 为侨海网专有标识。侨海网权属世界华人杂志社、洛杉矶国际时事通讯社、侨海网有限公司。
为侨海网专有标识。侨海网权属世界华人杂志社、洛杉矶国际时事通讯社、侨海网有限公司。